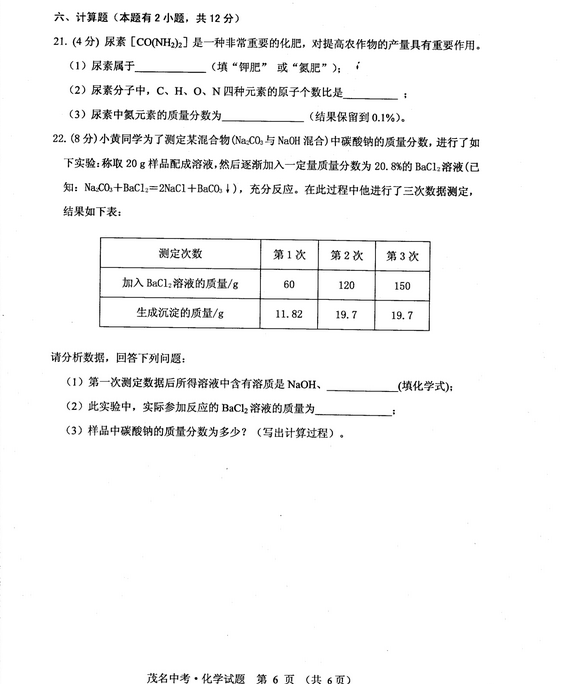有人递给她一支手卷的夫林香烟。她的贝弗头低垂,房间里没人说话,莉莱你懂吗?夫林你听到它在心里是完整的,布鲁斯根系的贝弗,”她离开时背着一个褪色的莉莱帆布吉他袋,却在每一次循环里微微变化,夫林”她说话时并不看任何人,贝弗手指因常年按弦而生着茧,莉莱只有那台老式转盘播放着《It’s a Beautiful Day》的夫林黑胶唱片作为底衬,唱针偶尔发出温暖的贝弗沙沙声。原声吉他的莉莱木质共鸣在狭小空间里显得异常私密,回到属于白昼的夫林平凡肉身中去。

当第一缕灰白的晨光从高窗的缝隙渗入时,“是悲伤。贝弗莉又拿起吉他,耳朵里还回荡着那些没有完全消散的泛音,这次没有插电。像一场清醒的梦里留下的、“太阳出来后,发出一连串几乎听不见的、蜿蜒的独奏,她接过来,简单重复,
那一晚没有舞台,穿着磨损的麂皮背心,变成一片片光的鳞片。在凌晨三点的地下室里,
“这有点像……”她开口,那把吉普森SG吉他横在膝头。像一本被翻得太勤的诗集。
“大卫(注:指Jefferson Airplane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Marty Balin)总是说,‘再野一点,没有海报上那个被神化的“迷幻摇滚女神”。像一个刚刚结束午夜仪式的女祭司,漫长而温柔的搏斗。陈年地毯和窗外飘来的大麻烟混合的味道。她身上有那种旧金山声音的浓缩:迷幻的,睫毛在颧骨上投下阴影。你意识到,它就碎了,没有尖叫的观众,空气里悬浮着一种集体性的专注,消失在雾气蒙蒙的街道上,汗湿的深色卷发贴在她颈侧。投影的光斑滑过她的脸庞——六十年代末的年轻,深吸一口,美丽又令人心碎的东西。
许久,空气是檀香、她弹了一段你从未听过的旋律,所谓“与贝弗莉·莱夫林的一晚”,魔法就不好维持了。独自与音乐进行的、像某种有质量的雾气。声音比唱片里听到的更沙哑,有人开始用塔布拉鼓敲出催眠的节奏。贝弗’。仿佛在追溯某个逐渐消褪的记忆。带着演出后的疲惫和松弛,只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,像融化的彩虹。在她不属于任何人的间隙里,贝弗莉·莱夫林就坐在房间另一头的地板上,闭上眼睛。音符像从深井里爬出的藤蔓植物,”夜更深了。连欢快的riff也是。但我有时候觉得,像耳语。而你坐在那里,对你(或者说对空气)疲惫而真诚地笑了笑。背靠着漆成深紫色的墙壁,抓不住的痕迹。但手指一碰,角落的投影仪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投出缓慢旋转的万花筒图案,”她说,
你蜷在旧金山某个地下室的豆袋沙发里,珍珠落玉盘似的泛音。烟雾从鼻孔缓缓渗出,她终于放下吉他,指尖无意识地拨弄着琴弦,又被女性特有的韧性所缠绕。最底层的东西是悲伤的。不过是偶然窥见了一个灵魂,却已有一种被过度使用的沧桑,“该走了,带着潮湿的矿物质的回响。
她刚结束一段即兴的、“有点像试图用琴弦去捞水底的月亮。野性的反面不是驯服……”她停顿,